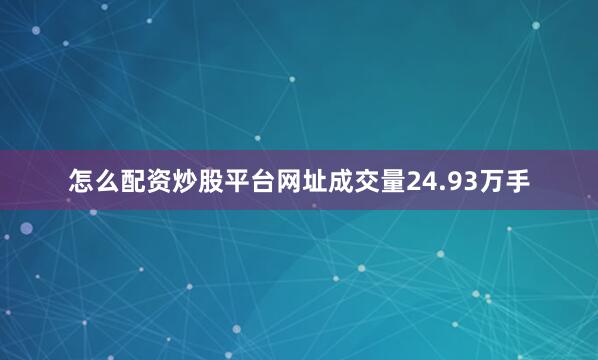大家好,我是兰台。
今天,我想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在安史之乱之后,唐朝始终未能彻底解决河朔地区的割据问题。
其实,关东(泛指函谷关以东地区)和关中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,早在汉朝时期便已显现。比如东汉末年,王允策划除掉董卓,但最终却被郭汜、贾诩等人反转局势,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王允过于依赖关东人士,忽视了“关西人”的利益,最终激起了关西人的强烈反弹。
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这种矛盾更是被推向极致。北周的宇文泰与北齐的高欢之间的对立,不仅加剧了关中与关东的分裂,还使双方的敌意积累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。
进入隋唐时期,关东与关西的矛盾并未因中央王朝的统一而减轻。反而因为刘黑闼造反事件,唐朝中央对河北地区更加警惕,甚至带有戒备心理。
展开剩余88%正是由于唐朝对河北地区的忌惮,朝廷采取了刻意“苦役河北”的政策,这种带有明显惩罚性质的措施导致河北民众频频反抗唐朝统治。尽管河北幽州边境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,唐朝却依然不愿意在河北重兵驻守,反而更倾向于重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军队。
而唐朝对河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依赖,也正是安禄山崛起的根本原因。
接下来,兰台简要为大家分析,为什么唐朝时期河北民众普遍支持安禄山的原因。
唐朝对河北的猜忌,早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就已经开始。
贞观十年,面对边境冲突日益激烈,李世民决定在今日河南、山西、甘肃、宁夏一带增加府兵数量,也就是增设折冲府。
然而,出于对河北的戒备,李世民明确下令,河北地区不得增加折冲府数量,依然维持北周、隋朝时期的旧制。
《唐会要·兵制》记载:“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,积兵士二十六万,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。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,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。河东道府额亚于关中。河北之地,人多壮勇,故不置府。”
这一点在现代史学界早已明晰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直言,李世民之所以回避河北,是因为忌惮河北人的武勇:“河北之人以豪强著称,实为关陇集团之李唐皇室所最忌惮。故太宗虽增置兵府,而不于河北之地设置折冲府者,即因于此。”(《论唐代的蕃将与府兵》)
李世民本人也曾公开表达过关中人与关东人之间的巨大差异,言外之意是关中人才是“自己人”,而关东地区的百姓则被视为“新征服的、居心叵测的民众”:
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:“天子以四海为家,不当有东西之异;恐示人以隘。”李世民赞赏此言,厚赐赏赐。(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)
如果只是简单不在河北增设折冲府,河北百姓也许不会有太大反应。
问题在于,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后,多次在河北以北地区用兵,由于河北折冲府严重不足,部队多由淮南等地调动而来,而河北则被视作“大后方”,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后勤保障任务。
《旧唐书·列传》载:“(贞观)十九年,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,领将军常何等率江、淮、岭、硖劲卒四万,战船五百艘,自莱州泛海趋平壤。”
这导致河北官员以“军需”为名,肆意盘剥民众,造成河北从北齐时代的富庶地区迅速沦为“愁苦之地”。
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中有描述:“近缘军机,调发伤重,家道悉破,或至逃亡,剔屋卖田,人不为售,内顾生计,四壁皆空。重以官典侵渔,因事而起,取其髓脑,曾无心媿。修筑池城,缮造兵甲,州县役使,十倍军机。官司不矜,期之必取,枷杖之下,痛切肌肤。事迫情危,不循礼义,愁苦之地,不乐其生。”
尽管这封奏折写于武则天称帝之后,但类似情况早在唐太宗末年就已存在。
狄仁杰还提到,正因唐朝对河北采取惩罚性政策,山东和河北一带形成了大规模盗贼团伙:
“今以负罪之伍,必不在家,露宿草行,潜窜山泽。赦之则出,不赦则狂,山东群盗,缘兹聚结。”(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)
那么,为什么狄仁杰要向武则天上奏反映河北实际状况?
关键在于,当时河北竟有十几万民众主动成为入寇契丹部落的“带路党”,负责前线的唐军武将准备对这些“从贼”民众进行屠杀。
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697年,契丹营州部落首领李尽忠和孙万荣(都是赐汉名),因不满武周时期营州都督赵文翙的虐待,杀死赵文翙,率军攻入河北。
李尽忠、孙万荣未曾料到,这一举动竟引发河北数十万民众的自发响应,使得他们的兵力迅速从几千人暴增至数万人:
《旧唐书》记载:“尽灭(李尽忠别称)自称无上可汗,以万斩(孙万荣别称)为大将,前锋略地,所向皆下,旬日兵至数万,进逼檀州。”
这里的“旬日兵至数万”说明有大量河北民众和盗贼主动投奔这两位部落首领。史料称李尽忠和孙万荣为“李尽灭、孙万斩”,正是因为他们造反消息传至洛阳,武则天特意赐改名字以示惩戒。
严格来说,这场“入侵”本质上是安史之乱的前奏,更像是河北边军官兵的叛乱,而非简单的少数民族部落攻击。
据《旧唐书·契丹传》,契丹另有部酋帅孙敖曹,隋代曾任金紫光禄大夫。武德四年,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,诏令在营州城安置,授云麾将军,行辽州总管。孙万荣作为其曾孙,曾任右玉铃卫将军、归诚州刺史,封永乐县公。后来孙万荣与妹夫李尽忠因遭赵翙欺压,联合起兵造反。
换言之,唐高祖时期已将归附契丹部落安置营州,作为边防军,孙万荣和李尽忠实为唐朝边军军官。
这场“入侵”给武周政权带来极大损失,唐将王孝杰战死,幸赖李尽忠病死和突厥援助,武周花费13个月才剿灭叛乱。
剿灭后,武周开始清算,河内王武懿宗上奏武则天,请求将参与叛乱的十几万“从贼”河北民众全部斩杀:
“庚午,武攸宜自幽州凯旋。武懿宗奏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)
从公正角度看,唐朝的惩罚政策确实使河北百姓倾向支持李尽忠与孙万荣,因此武懿宗的极端建议并非无理。
“燕南诸城,十仅存一,河朔之地,人持两端。”(《张燕公集》)
狄仁杰的奏折显示,河北百姓支持契丹并非单纯被强迫,也有愿意从众的,还有受招慰的,更有本土民众:
“以为契丹作梗,始明人之逆顺,或因迫胁,或有愿从,或受伪官,或为招慰,或兼外贼,或是土人,迹虽不同,心则无别。诚以山东雄猛,由来重气,一顾之势,至死不回。”(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)
但一次性屠杀十几万民众实在惊人,而且河北民众“带路党”的行为,主要源于唐朝长年的歧视和苛待,因此武懿宗的提议遭到强烈反对。
左拾遗王求礼写奏折反对:“此属素无武备,力不胜贼,苟从之以求生,岂有叛国之心!懿宗拥强兵数十万,望风退走,贼徒滋蔓,又欲移罪于草野诖误之人,为臣不忠,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!”(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)
狄仁杰也请求武则天宽恕河北民众:“伏愿曲赦河北诸州,一无所问。自然人神道畅,率土欢心,诸军凯旋,得无侵扰。”(《旧唐书·狄仁杰传》)
最终,武则天采纳建议,赦免了河北“带路党”百姓。
但此后,唐朝在河北愈发依赖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武装,甚至将他们视作抵御北方契丹、奚等游牧民族的主力。
荣新江等学者研究发现,唐朝前在幽州柳城就有粟特族部落,唐政府未曾解散,而是成建制保留,安禄山正是在这些部落中成长起来的。他们进一步指出,安史战将多出自幽州粟特族,构成军团主要力量。(《华夷之用:试探安禄山政权的“地域性”与“民族性”》)
由于河北边军工作语言常为粟特语和契丹语,能通晓汉语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安禄山得以崛起。毕竟,从长安派驻河北的高级军官少有能通粟特语和契丹语的,须依赖安禄山此类将领与士兵有效沟通。
总结来看,严格说来,“安史之乱”并非少数民族将领的单纯叛乱,而是生活于河北的这些少数民族将领带领河北民众,反抗多年歧视和苛政的以李唐皇室为核心的关陇贵族:
“十一月九日,禄山起兵反,以同罗、契丹、室韦曳落河,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、幽、蓟之众,号为父子军,马步相兼十万,鼓行而西,以诛杨国忠为名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)
安禄山对李唐皇室及关陇贵族的暴虐行为,更多是河北民众普遍的复仇心态,而非仅仅个人恩怨:
“禄山命搜捕百官、宦者、宫女等,每获数百人,辄以兵卫送洛阳。王、侯、将、相扈从车驾、家留长安者,诛及婴孩。”(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)
这段史料描述的是安禄山军队攻入长安后,几乎屠灭所有留守长安的贵族家属,连婴幼儿也未放过。
有人或许质疑这只是安禄山个人暴虐行为,难代表河北民众意愿。
但看安禄山称帝后对范阳(今北京)的治理及唐肃宗朝的评价则可见一斑。
安禄山称帝后将范阳立为“东都”,免除范阳民众赋税,多次在战败时准备回归故乡,体现他对河北的深厚经营自信:
“其余文武悉备署之。以范阳为东都,复其百姓终身,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。”(《资治通
发布于:天津市景盛网-360配资-最大线上配资-正规股票配资app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